對雄本團隊而言,空間的修復,始終是為了整合人與地方的關係。我們與新埔潘錦河故居的緣分亦是如此,透過與屋主家族合作,持續推進故居的整修與再生構思、「以終為始」煥發老屋新生命,讓故居在外觀與機能完好之外,更是連結過去與未來、串聯在地智慧與外部創意的節點。
本次走讀以「地方博物館」為概念框架,引導學生深入了解新埔的日常樣貌、釐清場域輪廓,並將田野調查的發現,結合潘錦河故居未來的空間計畫,提出具有在地意義的設計方案。透過課程的走訪,我們與新世代的設計者共同探索了地方與建築的關係,不僅作為課堂活動的延伸,也是潘錦河故居在進入下個階段前的保溫起點。
打開地方的多重視角
走讀活動從新埔遊客中心出發,雄本團隊首先向學生們分享了潘錦河故居的保存現況與持續再生的進程。我們深知,空間的生命力源於不斷延伸的對話與思考,因此邀請到擁有豐富地方知識的蔡榮光老師, 以「人文・地景・產業」的系統框架,帶領大家重新理解新埔。
蔡榮光老師從吳濁流的文學、陳定國的漫畫聊起,談到畚箕地形如何孕育凜冽的九降風,進而形塑了柿餅、米粉、烏魚子這「風的三種味道」,串連起新埔的自然環境與常民生活。透過蔡榮光老師的導引,我們看見了風土、產業與文化在地景中緊密交織的樣貌,也理解了地方記憶如何在日常中延續。

穿梭風水與巷弄,閱讀無字的歷史

跟隨蔡榮光老師的腳步,我們行走於「三街六巷九宗祠」的歷史脈絡中,穿過歲月與信仰的縱橫交錯,細看先民的智慧如何凝鍊於街巷肌理與建築表情之中。在和平街上,宗祠的櫛比鱗次並非偶然,而是源於『背山面水』的風水信仰——對家族與聚落永續的共同祈願。來到潘宅,與學生們分享那獨特「螃蟹穴」的故事:屋瓦忌紅、門前活水不絕。這些看似日常的禁忌,實則承載了先民對於安居樂業的想像,也是老屋再生所欲延續的文化底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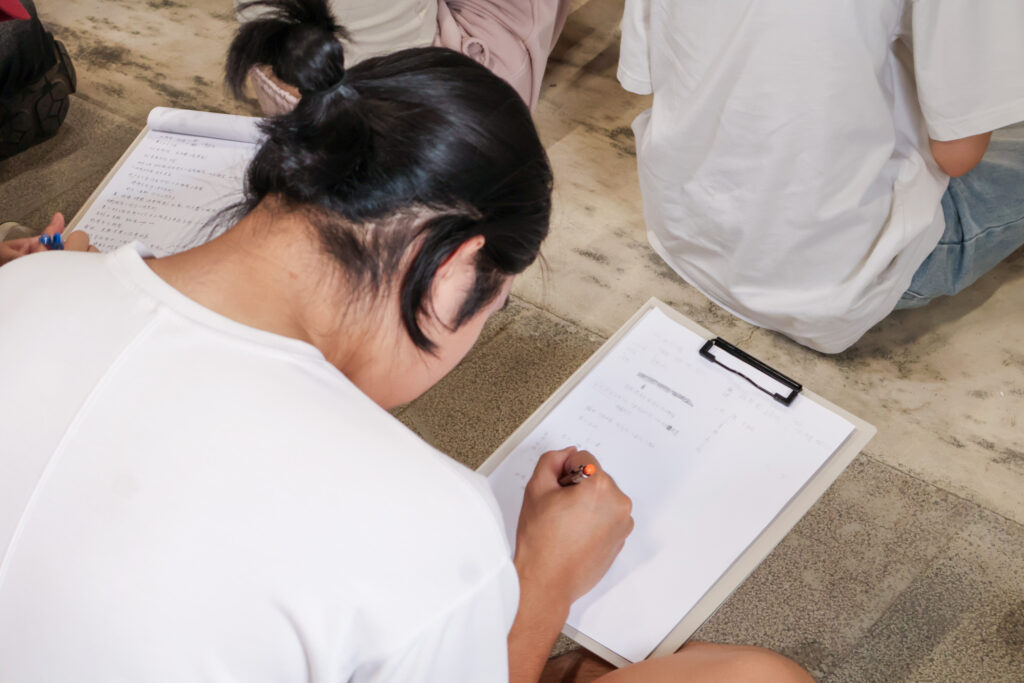
透過大尺度的新埔鎮地圖,蔡榮光老師引領地景設計學生思考新埔聚落藍帶與綠帶之間的關係,進一步說明近年在城鎮發展政策下,新埔鎮的景觀變遷。
導覽途中,蔡榮光老師亦提及在漢人墾拓史之下被隱沒的另一層記憶——平埔族道卡斯族的遷徙與消逝。那句「語言斷、文化滅、族群絕」的九字箴言,提醒著我們,每一塊土地都蘊含多元族群的歷史。在推動地方再生的同時,如何拾起這些被遺忘的故事,正是文化工作者持續思考的課題。

從潘錦河故居看見家族記憶與地方脈絡

經過潘宅後院,我們來到潘錦河故居,建築語彙在此悄然轉折,從傳統的漢式院落過渡到和洋混合式的洋樓。坐落於新埔中正路上的潘家洋樓,由曾任新埔鎮長的潘錦河先生親自設計,宅院從外表裝飾至內部細節、由結構設計到空間配置,皆承載著地方生活與社會變遷的多重脈絡。我們透過潘錦河故居,可以窺見地方仕紳在時代演變中的轉化,亦能看見一位長輩對子女與後代的關愛。
自日治時期建造至今,洋樓的使用狀態不斷演變,從住家、餐廳到如今即將轉型的多種可能性,不同階段皆留下了相應的印記;走進室內,從象徵家族門面的洋式客廳、潘錦河先生的起居空間,到家中穀倉的務實機能,跨時代的生活樣態具體而微地封存其中。
藉由潘宜珣的介紹,我們了解到每棟老房子都像年邁的長者,到了一定的年歲,身體都會面臨不同的挑戰與狀況——潘錦河故居也走到了這樣的關口。所幸家族願意凝聚力量,以修復工程延續其生命,在維持建築結構與在地歷史脈絡的同時,更留住了後代對於潘錦河先生的感念與記憶。
在課程導覽中,學生們藉由觀察屋舍間的天井、附有圓窗的個人書房、近代化的洋式客廳以及保留日式生活習慣的榻榻米,理解空間使用、建築形制與文化脈絡的關係。潘錦河故居從建築的保存,逐步走向生活體驗的再生,古今也在此交會,讓年輕世代得以感受新埔風土與時代故事。

從看見問題到尋找可能
當隊伍行至視野開闊的日本公園,俯瞰新舊交融的市街,方才一路走訪的線索彷彿逐漸匯聚成圖。走過巷弄、宗祠與市場,學生們對新埔有了更立體的感受,也提出了具啟發性的疑問:這些莊嚴的宗祠,除了作為家族祭祀空間,在當代生活中還能扮演什麼角色?而一個能持續運作的地方生態系,又該如何被建立?這正是雄本團隊不斷思索的核心課題——老屋新生,從不是單一的保存行動,而是一種「串點成線、擴線成面」的整合過程,也期盼潘錦河故居能夠成為持續與地方對話、收攏萬千可能的起點。
活動尾聲,學生依據主題分組,深入新埔的日常場域,造訪了在地知名的花奶奶米糕與義順冰店,並與店家進行簡單交流。當地方故事在耳邊響起,新世代的創意在歷史空間激盪,我們也在學習與傾聽之間,再次確認了陪伴老屋走向新生的意義——那便是讓老屋的故事被聽見,讓地方的未來被共同想像。


